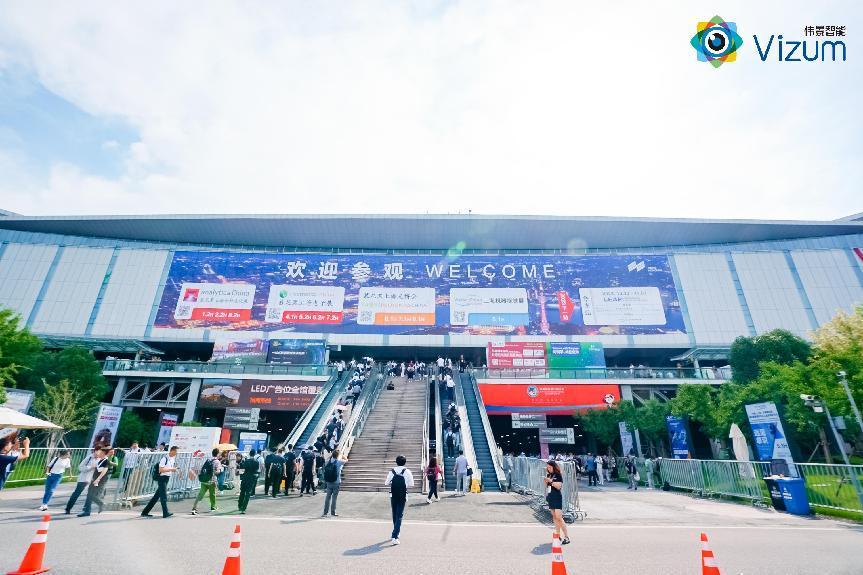策展人费雷德里克·保罗解读“面具”篇章。 视频:叶紫(02:16)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上海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常设展终章“肖像的映象”正在西岸美术馆对外展出。展览以“肖像”为线索,勾勒20世纪以来的众生百态。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为蓬皮杜中心当代艺术馆藏部策展人费雷德里克·保罗(Frédéric Paul),他以“肖像”透视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进程,在此“声名显赫”与“籍籍无名”的人物比肩,“肖像”成为从显贵到社会底层的众生相。与之平行的展览线索是,参展作品的艺术家中既有大批青史留名的明星艺术家,亦不乏诸多被忽视和遗忘的艺术家。
在多条平行的线索的交叠下,策展人费雷德里克·保罗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为展览的主题带来更多解读维度。
澎湃新闻:展览名“肖像的映像”(Les Miroirs du portrait),直译为“肖像中的镜子”。正如展览中所描述的“所有的镜子都会反射出我们呈现在镜子面前的事物的肖像”,也是作为忠实的“画家”。在展览中,“镜子”与“肖像”更为深层的关系是什么?
保罗:我认为镜子有很多面,不同角度看到的镜像是不同的。但在这里“镜子”是复数、“肖像”是单数。
肖像作为一个单独存在的、独立的艺术类型。当我们提及肖像,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绘画的一个种类。对我而言,肖像(或肖像画)并不是只有一个单独的历史,它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和路径。
展厅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在阐述或是描述这幅肖像过往的历史或者故事,同时这些故事的种类非常丰富,它们不是一个单一的故事,每一幅作品都在讲述着不同的故事。回到“镜子”这个概念上,每个人站在镜子面前,镜子所反映出的画面和场景也是不一样的。
马夏尔·雷斯,《一种自由的形式》,1969年,醋酸纤维塑料、玻璃、投影机、金属、上漆木板,尺寸可变
澎湃新闻:相比文艺复兴以来,肖像的目的更多是记录,20世纪至今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带给肖像哪些改变?如今的肖像旨在表达什么?
保罗:其实第三次常设展的15个篇章(主题),就是从15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肖像这个艺术概念不同的路径或不同的历史。15个篇章它所涉及的就是我们谈到肖像会经常考虑到的15个主要的问题。
展览现场,第一篇章“所有的色彩”中展出的作品。
第一个篇章谈到色彩和形象。在最早的古典绘画中,肖像使用更多的是棕色或者是中性调的颜色,色彩并不丰富,但是在现当代艺术中,它所呈现的色彩更加丰富。
弗朗齐歇克·库普卡,《黄色色阶》,1907年,布面油画,79×79厘米
第二篇章的主题就是“扭曲面部?”,因为肖像画原先的主要作用就是忠于原型。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艺术家创作所呈现的肖像与原型相比有很大变化,像立体派毕加索画的肖像,也许很多观众对其理解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展览其他的不同的篇章(如“到街头去”“家庭肖像”“世界女性”)都是一个个不同的社会场景和舞台,呈现出不同场景中的肖像的概念。在第一展厅的最后,有一堵墙,整个墙面是一幅作品,它其实是一个艺术拍卖会现场的场景,名人肖像和有战争意味的肖像呈现在同一个场景中,整个画面因为拉伸而变得扭曲。
展览第一展厅出口墙上的作品。路易丝·劳勒,《1945年后的生活(面孔)(可调适)》,2006-2015年,乙烯基墙纸,多尺寸
画面中左下戴着帽子的人,正好与展览最后一个章节“脱帽致敬!”首尾呼应,有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意味。总的来说,肖像的不同历史变迁路径,可以从这15个篇章中的不同视角逐一感知。
展览现场,第15篇章“脱帽致敬!”中展出的作品。
澎湃新闻:展览展出了雕塑、绘画、摄影等多个艺术门类,就肖像的历史而言,它们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摄影诞生后,带给肖像怎样的影响?
保罗:雕塑、绘画、摄影存在的历史是不一样的。三者中,摄影的历史是最短的,只有150年左右,但摄影的出现给肖像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具有颠覆性的。过去肖像往往是肖像的主人委托一位画家创作。古代钱币上也会印刻着名人头像作为纹章,但普罗大众是没有资格出现在肖像画中的。
马克·亚历山大,《吕西安·弗洛伊德的弗朗西斯·培根肖像》,2006年,木板油画,17.8 ×12.8厘米
其实,在摄影刚问世的时候,带给肖像的变化并不大。最早的摄影师数量很少,大部分还兼职于画家的身份。很多摄影师(或画家)首先以自己或者亲近的人作为拍摄对象。当时需要人们到照相馆坐在镜头前面,保持静止不动,如同画一幅肖像画一样。同时,在那个时候要成为摄影师镜头前被拍摄的对象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能做到。
佚名,《阿诺德·勋伯格肖像》,1911年12月12日前,明胶银盐印相,11.2×9厘米、底纸: 20.5 x 12.8厘米
后来出现了街拍的形式,可以在运动状态中捕捉到很多镜头,这是摄影带给肖像最大的变化,我们可以把动态引入到肖像画面当中,可以走出摄影棚、工作室,到大街上去拍社会纪实场景。随着摄影技术的普及,各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一技术。当时摄影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创作的纪实性、客观性,拍摄的作品可以用作留存的证据。
吉赛尔·弗罗因德,《詹姆斯·乔伊斯从出租车上下来,巴黎》,1938年,银盐冲印照片
40×30厘米
澎湃新闻:因为摄影发展,“籍籍无名”也开始被记录并在展览中与“声名显赫”的人物比肩,“声名显赫与籍籍无名”也是展览15个主题之一,并成为始终贯穿的线索。如何想到使用这两组人物在展览中并置?
保罗:整个策展过程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在他拍摄了一系列摄影作品(在1892至1954年间拍摄的500多张照片集结起来,并赋予了“20世纪众生相”这一标题)中,我挑选了很多的社会名流和无名之辈。在桑德的系列摄影作品中,他构建了八个类型的社会阶层,每个社会阶层都反映了当时时代和社会不同的面貌。其中既有政治人物、艺术家、工业家等等,也可以看到很多流浪汉或是普通人。我并没有按照原来桑德的八个社会阶层来做策展,而是将这群人分成两个大类型——社会名流和无名之辈,但我也依然遵循或者说延续桑德在创作中所考虑、关注的一些问题,即“这些社会人群的共通之处有哪些?”
奧古斯特·桑德,企业家《温布伦纳,黑尔多夫》,1911,银盐冲印照片
奧古斯特·桑德,《火柴小贩》,1927年,银盐冲印照片
虽然类似的摄影作品数量有很多(数百件),但在整个策展和筹备的过程当中,我主要考虑的是把最具鲜明对比的照片(或是摄影作品)放在一起作对比。比如,《企业家温布伦纳》(1911年)和《火柴小贩》(1927年)这两幅作品之间的对比,我特别想告诉观众的就是桑德在他作品中体现的一个特殊性。
而对于那些著名的艺术大师以及被遗忘的艺术家们,我们也采用了相同的布展原则,将他们一同展示。
展览现场,左:凡·东根《演员波莱特·帕克斯》,1928年,布面油画,230×110厘米;右:格里高里奥·西尔蒂安,《罗马卖花女》,1925年,布面油画,213×115厘米
澎湃新闻:展览中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的死亡面具得到了三重“再现”:曼·雷所拍摄的石膏原样,雅克·利普希茨(Jacques Lipchitz)制作的青铜件,以及将在之后替换展出的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ész)在莫依斯·基斯林(Moïse Kisling)工作室拍下的青铜件的照片。如何看待这三者的关系?
保罗:首先很遗憾,此次展览没有莫迪利亚尼的作品,因为蓬皮杜中心拥有莫迪利亚尼的作品数量非常少,可以作为外展的两件目前都有别的用途。
但在策展过程中我非常幸运、机缘巧合中发现了安德烈·柯特兹的摄影作品。这件摄影作品在莫依斯·基斯林工作室里拍摄的,照片中的书架上放着莫迪利亚尼的遗容面具,我看到之后感触颇深。此次展览将持续18个月,摄影作品每半年将做一次轮换。安德烈·柯特兹在莫依斯·基斯林工作室里拍摄的照片将在第二次轮换中出现。
安德烈·柯特兹,《基斯林工作室》,1933年,银盐冲印照片(第二轮展出)
莫依斯·基斯林是莫迪利亚尼最好的朋友,基斯林昵称莫迪利亚尼为“莫迪”。在莫迪利亚尼去世之后,基斯林完成了第一个莫迪利亚尼的石膏遗容面具,这也是曼·雷所拍摄的石膏遗容面具的原型。
在柯特兹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在基斯林工作室书架上,除了莫迪利亚尼的遗容面具,还有莫迪利亚尼画的妻子珍妮的肖像。珍妮在莫迪利亚尼去世之后殉情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基斯林和莫迪利亚尼之间深厚的友情,也能看到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但这个作品中也有幸福、圆满的一面。在莫迪利亚尼的遗容面具下面还有另外一张照片,是基斯林全家在海边度假的全家福。
雅克·利普希茨,《莫迪利亚尼死亡面具》,1920年,铜绿青铜,23×14×12厘米
因为上述渊源,所以莫迪利亚尼的形象在这次展览中以一种非常玄幻的方式得到了三重体现。曼·雷所拍摄的石膏遗容面具、安德烈·柯特兹在莫依斯·基斯林拍得照片,以及雅克·利普希茨根据曼·雷所拍摄的石膏原型做成的青铜面具。展览中,青铜面具会在展期内持续地展出。曼·雷和柯特兹的照片将轮换展出。开展之后首先看到的是曼·雷的照片。
曼·雷,《亚美迪欧·莫迪利亚尼遗容》,1929年,银盐冲印照片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有出现艺术家的肖像照、自画像,以及被别人所画的肖像画。在您看来,艺术家本人是如何通过图像营造自己形象的?
保罗:当艺术家创作自己的肖像画时,首先是为了满足一种骄傲的情怀,他觉得有为自己画一幅肖像画的价值和必要。在展览中我们还有主题称之为“怪诞”的部分,这是另外一种艺术家的肖像和自画像的呈现方式。
有时候,艺术家也会给自己的艺术家朋友创作肖像画,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或感谢,也有可能是艺术家之间共通的语言,是他们互相理解的一种方式。
比如,当一位志向远大的艺术家看到他的艺术家朋友以他的面容画了一幅肖像画,他就可以从中感觉到那位艺术家创作的初衷、出发点和理念是什么,同时也会甄别出和认识到那幅肖像画与他本人之间存在的差距是什么。
展厅里有这样一组作品,一件是夏尔·卡穆安在1904年画的阿尔贝·马尔凯(Albert Marquet)肖像。马尔凯是马蒂斯的挚友,在那幅肖像画中的坐姿挺拔,可以感受到人物形象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活力。在这幅画的旁边是同一年马尔凯画的《安德烈·鲁维尔》。
展览现场,阿尔贝·马尔凯作品《安德烈·鲁维尔》(左)和夏尔·卡穆安作品《阿尔贝·马尔凯》。
又比如,在艺术家的肖像和自画像主题中,有着整个展览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件作品——1895年凡·东根(Kees Van Dongen)创作的自画像,在这个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把自己形象化,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画笔正在创作,给人一种充满自信、很有感染力的感觉。
凡·东根,《自画像》,1895年,布面油画,92.5×59.8厘米
这样的肖像画我们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但也有一些肖像画的寓意则更为微妙和深远。在整个展览中最为深奥和难以理解的,或者说是最跳脱玄幻就是克劳德·克洛斯基(Claude Closky)的《我最爱的20分钟》。这是一个视频作品,视频拍摄了一个电子表,上面不断跳动着表示小时和分钟的数字。在这个画面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处出现艺术家本人的相貌,只有不断跳动变化的数字,但是通过这些数字,艺术家告诉观众“请相信我,这些数字能够充分体现我的主观意义”。比方说“11:11”就是克洛斯基最喜欢的一个时间点,没有什么特别讲究,他就是喜欢。这个作品持续20分钟,我们看到的是有着阿拉伯数字的、克洛斯基的手表,上面的数字每一分钟就会跳动,作为观众,我们其实不得不跟着画面、跟着艺术家去体验这20分钟,等待那些数字的跳动,体验艺术家在数字变化背后想带给我们的感受。
展览现场,克劳德·克洛斯基的作品《我最爱的20分钟》
澎湃新闻:展览中有培根(Francis Bacon)通过绘画向梵高(Van Gogh)的致敬、罗贝尔·康巴(Robert Combas)向迪士尼(Walt Disney)致敬,以及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向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致敬,如何看待他们不同的“致敬”方式,尤其是马格里特是否是一次颠覆和调侃?
保罗:首先了解一下马格里特和路易·大卫的背景,路易·大卫是一位法国艺术家,他也是一位革命者,波旁王朝复辟后,他被迫流亡比利时。马格里特是比利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创作这幅作品既是向大卫致敬,又带有一定的幽默色彩。他借用的是路易·大卫的一幅非常有名的绘画作品《雷卡米耶夫人像》,他复刻了大卫绘画当中的场景,在装饰或是家具的描述上,忠于原作的,但是唯一变化的就是雷卡米埃夫人本人。
路易·大卫,《雷卡米耶夫人》(非此次展览展品)
我们在马格里特的作品中看到的不是一位女士,而是像人一样坐在长椅上的一口棺材,也就是说雷卡米耶夫人本人已经躺进了棺材里,可以说它带有善意的幽默和讽刺的调性,也作为超现实主义表现的一种手段。这是马格里特向在上个世纪动荡的历史中迷失的法国人路易·大卫致敬。
展览现场,马格里特的青铜雕塑《大卫的雷卡米耶夫人像》
另外,其实马格里特所挪用的《雷卡米耶夫人像》原作其实并未完成,原作中的色彩还有一些有失调和的地方。我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我认为是马格里特借用自己超现实主义方式完成了路易·大卫的未完成的作品。
而培根对梵高的情谊和敬意是毋庸置疑、且非常深厚的,这和马格里特与大卫的关系完全不同,在《风景里的梵高》中没有任何幽默的色彩。在培根的画中我们看到梵高作为一个很小的人物形象出现,这也是梵高在培根心目中最深处占据的位置。相信纵观整个艺术史,梵高可以说是向其致敬的艺术家最多的一位人物。
弗朗西斯·培根,《风景里的梵高》,1957年,布面油画,153×120厘米
另外,罗贝尔·康巴是20世纪80年代自由形象画派的领军人物。他作品中很多灵感来自于民俗故事和民俗艺术形象,此次展览中的这幅作品中,他画的并不是忠实于动画原型的米老鼠。正如康巴自己所说的,“这是我自己的米老鼠,我想怎么画就可以怎么画”。这也是为什么画中他用法语写了——米老鼠不再是迪士尼的财富,而属于我们所有人。
展览现场,罗贝尔·康巴作品《米奇》,1978–1979年,丙烯颜料绘于硬质纤维板上,141×80厘米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有五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你认为他们处于怎样的现代、当代艺术脉络中,展览又如何解读这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保罗:的确在第三次常设展中有五位中国艺术家,分别是黄永砯、张晓刚、常书鸿、张培力和赵无极。他们分布在不同的篇章当中。在第二个篇章“扭曲面部?”中看到的是黄永砯的作品;在“家庭肖像”中,有两位艺术家(常书鸿和张晓刚)的,至于为什么只有这个篇章中出现两位中国艺术家,其实只是策展过程中的一个巧合。赵无极在“致敬”篇章和张培力在“世界女性”篇章。
黄永砯,《蒙娜-芬奇》,1986 – 1987年,布面油画切割,木、金属、玻璃、纸、灯泡,灯箱:33×28×13厘米,画布:165×126厘米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些中国艺术家在法国的知名度各有千秋。其中,赵无极和黄永砯是五人中最为法国人熟知的,对其他人的熟悉程度相对低一些。这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作为此次“肖像”展的一部分,首先是为了体现中国艺术家在肖像这个艺术领域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此与他们同时期的西方的艺术家进行对话。
常书鸿,《沙那肖像》,1935年,布面油画,46×38厘米
另外我也有一点私心,将五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纳入,让我自己以及其他法国艺术界人士能够对这些艺术家和他的作品有更深的了解和学习,最终想体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的过程。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常设展“肖像的映象”,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比如展览中,赵无极和陈列在他对面的马格里特向路易·大卫致敬的那部作品,其实都是以一种隐晦比喻的方式去向某人致敬、缅怀的一个过程,形成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对应。
赵无极《10.03.72 – 纪念梅》,1972年,布面油画,200×525.7厘米
澎湃新闻:如同摄影技术曾经被认为会替代肖像,AI技术是否会替代摄影?摄影记录的是真实还是虚构?
保罗:对于AI 技术是否会替代摄影,我认为答案非常简单——不会。因为我认为人工智能需要事先存储很多图像的信息,然后才能进行学习模仿和再处理。那么这个预先设定的图像信息来自于哪里?当然是来自于摄影和相机。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常设展“肖像的映象”,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至于摄影记录的是真实还是虚构?其实与“镜子”反映出画面是一样的道理。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镜子,镜中所见也是不同的,而会发生变化。我们看哈哈镜,它体现出来的是真实的人,还是“扭曲的人”?所以我们在进行人脸识别时,摄像头需要我们做出一些动作(眨眨眼或转头等)补充识别信息。
归根结底,摄影它呈现的既是真实也是虚构,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摄影已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史蒂夫·麦昆,《面无表情》,1997年,PAL制式录像带,黑白,无声,时长:4分03秒
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11月5日,期间摄影作品每半年轮换。